转自:潘乐
140年前,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世长辞。他的葬礼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——
哥·雷姆克代表《社会民主党人报》和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进献花圈,恩格斯发表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,马克思的女婿用法语宣读挽词,威廉·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演说。
当时,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对马克思去世讳莫如深,但“在整个欧洲和美洲,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,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、爱戴和悼念”。
在法国和西班牙,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的葬礼致唁电;纽约制桶工会为马克思举行追悼会,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会堂;布鲁克林工人文化宫为马克思降半旗致哀;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的学生和团体为马克思募捐花圈,恩格斯专门对此表示感谢。
世界各国的进步报刊还纷纷发表讣告、社论,将马克思评价为“无与伦比的学者”“工人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导师”“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”“推动地球运转最卓越的人物之一”,等等。
透过马克思的简约隆重葬礼,透过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,可以看到近代社会一些深层思想观念“质的飞跃”。
18世纪的博物学开始将人类身体视作一种物质机制,灵魂、精神和身体一样属于自然的一部分。在此基础上,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有决定意义地剪除了“彼岸神学”对生命过程的干预。细胞学、生理学、组织学等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,进一步使得人们能以一种系统的、全面的方式来对待生死。
19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一种新型生命权力观念:它不再通过“使人死”以彰显权威,而是通过“使人活”以使社会获得增益。
与之相伴,平民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工业革命在制造财富的同时,制造了大量的贫困和非自然死亡。恩格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中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生活、健康和劳动的悲惨现实——
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;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,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,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;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、破烂的或不结实的,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、掺假的和难消化的。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,工人饱受肺结核、猩红热和伤寒的侵袭。
根据恩格斯的摘录,1840年,利物浦贵族、自由职业者等上层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5岁,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,工人、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孩子,有57%死于5岁以前。
鲜明的社会分裂与残酷的社会现实,激发并坚定了马克思、恩格斯从事革命的决心。
和19世纪整体的死亡观念一样,马克思认为个体的死所遵循的是自然必然性,无需彼岸的救赎和外在的夸饰。马克思晚年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坦然说道:“当然,到了一定的年龄,因为什么而‘去见上帝’,完全是无关紧要的。”
在马克思看来,做一名共产主义者,理应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。也正因为如此,马克思去世后,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提议为其建立一座纪念碑时,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都予以拒绝。
正如威廉·李卜克内西所评价的,马克思并不要立什么纪念碑……在千百万因他的号召而已经团结起来了的工人们的心底里和脑海中,他不仅有一个比青铜更耐久的纪念碑,而且有一片生气勃勃的土壤。在这土壤上,他所教导和希望的一切,都将生长成——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生长成了——实际行动。
(作者: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潘乐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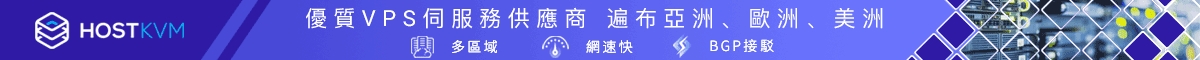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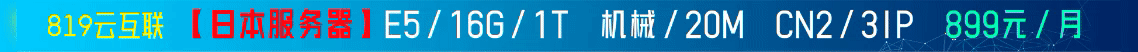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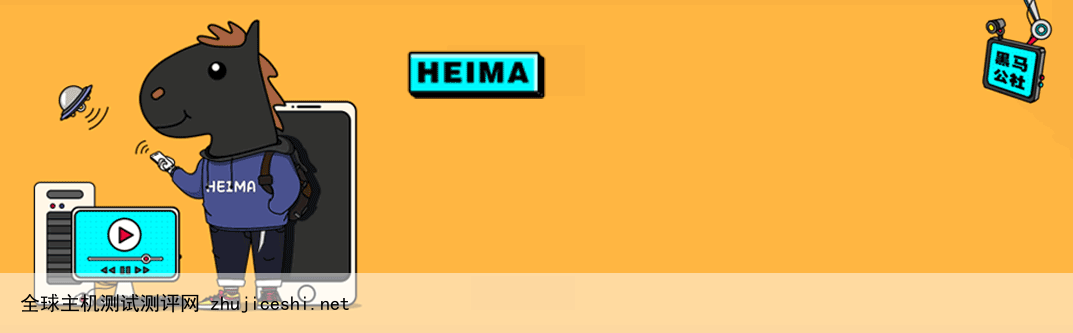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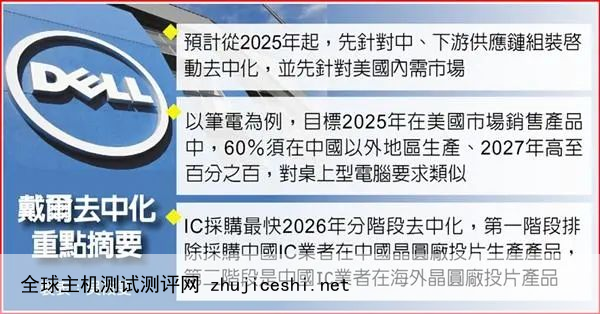

0 留言